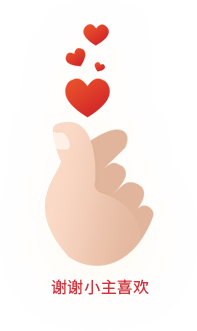关于回购权,北京法院最新判例破了最高院“6个月”法则

最近,北京二中院的一起股权回购纠纷判决,引发了创业、投资圈的热议。
在这起案件中,投资人因对赌失败,要求创始人回购股权,但距离回购条件触发,已过去近两年。
法院最终支持了投资人的诉求。
其认为,回购权属于“债权请求权”,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——而非最高院此前提出的,“6个月合理行权期”。
2024 年,最高院在法答网答疑中指出,“回购权的性质和行使期限争议较大,未直接定义其法律性质,但建议在无约定时以6个月为合理期间。”
这被广泛解读为,若协议未约定行权期限,投资人应在触发对赌条件后6个月内主张权利,否则视为放弃。
这一规则背后的逻辑是,回购权本质是,投资人“单方面决定退出还是继续持股”的选择权,类似合同解除权,需尽快行使,以稳定公司经营。
而北京二中院的判决,更倾向于将回购视为“要求对方付款”的普通债权,这给了投资人更长的缓冲期。
两种思路的冲突,本质上是对“效率优先”还是“保护投资者”的价值取舍,也暴露出司法实践中,对回购权性质认定的分歧。
而在经济低迷、创业与投资双双遇冷的当下,这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,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焦虑。
对创业者来说,若回购权被认定为“6个月除斥期间”,一旦投资人集中行权,可能让本就脆弱的现金流雪上加霜。
对投资人而言,若遵循“三年诉讼时效”,则面临长期“被套牢”的风险,影响资金周转效率。
而在司法实践上,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将是,协议条款的效力因地而异,“同案不同判”,对市场信心不利。
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“壮大耐心资本”,正是呼吁建立更稳定的投融资环境。而回购权,正是与此相关的一个关键议题。
这个方面,国外成熟投融资市场的做法或许会有参考性。
欧美等成熟市场里,通常设为“公司回购”,而不要求创始人个人承担,而且执行上不能强制清算公司,法院会注重公司独立人格。

查询美国关于回购权诉求的判例,发现实际上很难执行。

比如,某判例中,董事会认为,资金应保留用于运营,拒绝回购。
法院支持董事会的决定,认为“合法可用资金”不仅指账面现金,还包括公司运营所需资金。
另一判例中,法院认为,尽管公司有合同义务回购股份,但董事会仍需履行对所有股东的受托责任。
“若为满足回购而牺牲公司长期价值,可能构成对普通股东的不公”。
国内市场则有所不同。
回购条款更偏向于投资人,往往要求创始人“兜底回购”,因回购导致公司清算、创始团队破产的案例更是常见。
启明创投邝子平说,回购条款对投资机构有一定的保护意义,“但回购应有个前提:不把企业或创始人逼上绝路”。
他认为,回购权强制执行可能导致“共输”局面——企业破产、投资人损失、科技发展受阻。
这就需通过一级市场的耐心、二级市场的开放及监管支持,给予企业和创业者喘息空间。
-END-
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(ID:ctoutiao),给您更多好看的内容。